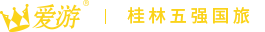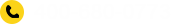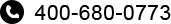李秉绶的兰竹图
来源网站:2 发布日期:2007-04-04
穿过叠彩山的风洞,到达北牖洞,便会见到不少古代的碑刻,给人印象最深的数李秉绶的兰花图和墨竹图。李秉绶(1748—1823)字云莆,号竹坪,是清代著名画家兼诗人,祖籍江西临川。李秉绶曾到京城任工部都水司官职,但嫌公职缠身,出作不便,壮年时就辞去官职,专心画事,后长期定居于桂林榕湖西岸,并在叠彩山的白鹤洞下修建画室,取名“环碧园”。当时在桂林的文人墨客常聚会园中,谈古论今,研讨画技。
他的父亲叫李宜民,在乾隆末年来桂林谋生,成为富商,李秉绶随父亲来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李宜民曾据浙江杭州圣恩寺里唐末五代僧人贯休所作的“十六尊者”(罗汉)像刻本勒石,碑原置桂林西山的隐山华盖庵,今存七星公园桂海碑林处。李氏一门子孙都出类拔萃。长子李秉礼,擅长诗文;次子李秉钺(yuè 音月),强于篆体隶书,山水画也十分飘逸雅致;三子李秉铨,不仅书法出众,尤以绘画墨兰而闻名;幺(yāo)子(排行最末的)李秉绶,擅长书画,所绘兰竹梅石尤佳。
李秉绶的墨竹图,枝叶繁茂,布局匀称,行笔秀丽,潇洒逸脱,有密而不繁、疏而不漏之感。相传墨竹图的创始人是元代的管仲姬,名道升,字仲姬,浙江吴兴人。她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fǔ 音俯)之妻,多才多艺,画墨竹兰梅,独出手眼。据说管道升画竹子的方法比较特别,当时管道升的窗前种有许多青竹,每当阳光将竹影映在窗帘上时,她便用墨照窗上的竹影勾画下来,成了一幅形象逼真的青竹图,于是“墨竹画”就成了一种艺术流派流传下来。
据说在元代,由于元朝皇帝的野蛮统治,许多画家因为画了一幅画就招来杀身之祸,画家们只好把满腔的愤懑泄于画面之上。据传元代画家郑所南曾作一幅有根无土的兰花,以此告诫人们国土已沦亡。封建社会的文人当国家民族处于逆境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常借用它们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梅、兰、竹、菊自宋以来就被称为“四君子”,象征清高、幽洁、虚心、隐逸。李秉绶兰花图中的兰花也是有根无土,导游们猜测这也是暗喻清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行将夭折。竹叶刚健似箭,修长的兰叶衬托着美丽的兰花,生机勃勃,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表现了他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傲岸精神。
位于李秉绶的兰竹图上下还刻有两首诗,这是清代诗人吕坚在清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年)腊(十二月)八日所题,高度赞扬了李秉绶兰竹图的价值,尤其是画竹的水平。李秉绶所画的不是普通的竹子,而是有特别内涵的“湘妃竹”。
这源于典故“舜妃啼竹”。虞帝(即舜帝)原是皇帝的第七世孙,他勤劳朴素,博得人民的拥戴。尧帝因年事已高,并经四方首领的推荐,确定把舜作为他的继承人。尧先是决定把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妃,并对他考查三年之后,才将帝位禅让给他。舜继尧位后,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娥皇、女英对舜也十分敬重,情深义重。舜不顾年老,还到南方各地巡视,曾游于桂林虞山下的黄潭。后舜南巡时死于“苍梧之野”(即今湖南九嶷山一带),噩耗传来,娥皇、女英二妃闻讯追去,一路悲泪奔涌。她们的泪血洒在竹林里,竹子上滴满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变成了美丽的斑竹。后双妃因悲恸而死于洞庭湖君山。舜又称“湘君”,故二妃亦称“湘妃”。她们所洒泪血变成的斑竹,也就称之为“湘妃竹”。桂林虞山公园中的“舜祠”(俗称“虞山庙”)是怀念和崇敬舜帝及双妃而建的,为桂林最古老的庙宇。此后,人们常用这一典故表现思念、忧伤的感情,或者用以咏竹。难怪吕坚在李秉绶的画上题诗并写记赞美道:“今见云莆画,长似听山阳(按古代方位的说法,水之北为阴,山之南为阳。晋向秀经山阳旧居,听到笛声而怀念亡友,因作《思旧赋》。后人以“山阳笛”为怀念战友的典故)笛也。”意思是说见李秉绶兰竹图,倍感亲切,就好像听到了山南边飘来的笛声,动听极了。
李秉绶在桂林的兰竹图石刻共有四组八幅,各有特色。除了在叠彩山北牖洞这两幅外,在伏波山望江阁旁(即过去的“大悲古洞”西侧)、七星公园里普陀山上的四仙岩(七星岩入口北侧,“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坏,现复制品移至桂海碑林)和虞山公园里韶音洞内,分别刻有两幅。伏波山这一组构图巧妙,可分可合。分开可作单独的两幅,如两幅合在一起,依然兰竹相接,疏密有序。虞山公园这一组兰竹画得清丽卓绝,风姿绰约。七星公园(桂海碑林)这一组,其中一株竹茎粗壮,枝梢迎风飘举,名为“风竹”;另一株竹叶低垂,如浴夜雨,名为“雨竹”。
上一篇:马相伯像
下一篇:游客如何搜寻有价值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