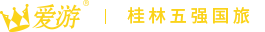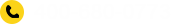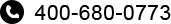马思聪抗战时期在桂林的音乐活动
来源网站:2 发布日期:0000-00-00
2007年5月20日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去世20周年的日子。马思聪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他毕生致力于中西音乐艺术的融合,以卓越的演奏与创作,使源自西方的小提琴音乐成为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并在中国广为传播。抗战期间,马思聪曾三次旅桂,在桂林文化城从事的音乐活动是多方面的。据专家统计,马思聪在桂林共举办过120台、280场次的专业音乐会。在这位音乐才子逝世20周年之际,文化天地版特别发表王小昆的文章《烽烟里的琴弦》,与读者共同回顾马思聪先生在抗战烽火中演绎的音乐人生。
我国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抗战期间,一共来桂林三次。第一次是1941年6月8日,马思聪及夫人王慕理由渝来桂。6月12日文化界著名人士在乐群社西餐厅举行茶会,欢迎马思聪夫妇,著名戏剧大量欧阳予倩(时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向光临的艺术家们致词介绍,席间艺术家们表演了节目助兴,马思聪也演奏了其创作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优美动人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这些背井离乡、逃难来桂林的艺术家们的心灵,思乡之情油然而生。6月14日,马思聪在大华饭店招待了桂林市新闻界。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桂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音乐会的准备工作才就绪。1941年6月20日,马思聪在广西戏院举行了抵桂持的第一场小提琴音乐会,连演了三天。演奏的曲目有德沃夏克的《印第安悲歌》,萨拉蒂的《西班牙屐舞曲》《流浪者之歌》,柴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格里格的《小夜曲》等世界小提琴名曲之外,还有马思聪的《思乡曲》《第一奏鸣曲》《史诗》《塞外舞曲》等等,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此时,正值“皖南事变”过后不久,寒气未消,阴霾未除,马思聪的音乐会给桂林抗战文艺舞台带来了清新的风,给苦难民众予强烈的震憾和慰藉。6月24日,桂林版《扫荡报》副刊发表了留德归来的马卫之(著名学者马君武之子)的观后感《马思聪先生提琴独奏会的第一晚》,著名作家孟波发表了《诚挚的谢意——致马思聪先生》的文章,均对演奏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月26日,马思聪又应桂林广播电台之邀,在该台播奏了《思乡曲》《塞外舞曲》及《牧童晨歌》(克莱斯勒曲)。尔后不久,马思聪离开桂林,经广东曲江(战时广东临时省会)抵达香港。
同年9月9日,著名学者司马文森、焦菊隐等在桂林创办的综合性刊物《艺术新闻》创刊号上,发表了马思聪的名作《思乡曲》正谱。《思乡曲》这首脍炙人口的小提琴曲,是马思聪创作的《内蒙古组曲》之二,它以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为主题,略带忧伤、怀念的情绪,在乐曲展衍过程中,以中国民间音乐常用的加花变奏的手法加以发展,把音乐的情感递次推进到高潮,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马思聪在桂林多次演奏了这首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名曲,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马思聪第二次抵桂是1942年3月24日。当时香港已沦陷敌手,很多旅居香港的文化人,纷纷转移至桂林。桂林媒介天天都在报道从香港脱险抵桂的人员名单和消息。关于其这次抵桂,媒体报称:“小提琴家马思聪偕夫人王慕理、家人及学生多人由粤抵桂暂居。”显然,马思聪这次抵桂,明显带有逃难性质。他这次在桂林住了半年,参加的文化活动也比较频繁。
1942年5月29日,桂林版《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作家徐迟和马思聪的《关于音乐的二封公开信——纯粹音乐、标题音乐、舞蹈、歌剧、世界性、民族性》,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这是马思聪抗战期间在桂林发表的第一篇音乐理论性文章。就上述问题,马思聪认为:“说起来,音乐实在是艺术当中之最神秘者,要好好地去解释音乐,几是不可能,或者都是一种高深的哲学。”关于“纯粹音乐”与“标题音乐”,这在抗战时期的桂林音乐理论争鸣中,曾一度是个敏感的话题。前不久,各报刊之间还发表过观点不同的文章争鸣,只是由于桂林版《救亡日报》的正确引导,才使这场争论平静下来。马思聪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纯粹音乐胜于标题音乐,其原因是在于纯粹音乐能永远令人产生常新的联想。”说到舞蹈,马思聪认为“音乐加形象,即舞蹈”;“音乐加形象再加文字,即歌剧。”马思聪还说到:“在我,纯粹音乐应是最高的表现,但舞蹈Ballet也是被人视为极完善的艺术形式,歌剧虽然是杂种之中最杂的,但我希望将来能够尝试一下……”。
1942年5月30日及31日,马思聪在国民戏院举行了第二次抵桂后的首场音乐会,演奏曲目除了上次在桂演奏的一些曲目外,还增加了拉罗的《西班牙交响乐》,以及其创作的《西藏寺院》《剑舞》和《摇篮曲》等四首曲目。5月25日重庆版《新华日报》在预报这场音乐会的消息中说到:“以一部分收入作为救侨之用。”
1942年8月22日及23日,马思聪弦乐钢琴演奏会再次在国民戏院举行。除了独奏上述一些曲目之外,他还演奏了莫扎特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第一小提琴马思聪、梅振汉担任。王慕理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乐队的协奏部分,就由马、董、林、梅弦乐四重奏代替。1942年9月3日,桂林版《扫荡版》副刊上发表了陆华柏《马思聪弦乐风琴演奏会听后感》的文章。陆认为:“马思聪先生的小提琴无论在技巧与表现方面,可说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此期间,马思聪还创作了几首歌曲,并经常出席一些旨在为宣传抗战的招待会和社会音乐活动,为抗战服务。例如1942年5月25日,出席了广西省紧急救侨会在乐群社举行的茶话会,与会者有茅盾、梁漱溟、金仲华、蔡楚生等。7月25日,出席了由桂林市中国银行、中国旅行社等18个机关团体举行的茶话会,招待前来中国参战的美国飞虎队,并在会上演奏了《思乡曲》《履舞曲》。写到这里,实在有必要对这次茶话会的起因作一简要介绍:抗战以后,桂林人民备受日军飞机空袭之害,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著名音乐家张曙父女抵桂仅一个星期,惨死在敌机的轰炸之下,就是一例证明。1942年6月12日,敌机又一次袭扰桂林,驻桂的美国飞虎队员驾机迎击,取得一次歼灭敌机八架的辉煌战绩。自此次空战第二天起,各界群众百姓,纷纷捐款捐物,开慰问飞虎队。这个活动持续了两月有余,马思聪参加的这场招待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1942年8月12日,桂林市总工会工人福利委员会举行游艺晚会,马思聪也在会上独奏了小提琴。
同年11月1日出刊的桂林版《新音乐》月刊5卷1期上,发表了马思聪《创作的经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真诚的散文诗的笔调,回顾了他“从一个音乐热烈的爱好者转为音乐专门学习者”的经过,描述了他留法期间与小提琴老师奥别多菲尔及作曲老师毕能蓬的师生之情及对他的影响;说到他在巴黎听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曲》时的“疯狂的喜悦”;记述了他从11岁“最早的创作的动机”至目前正在进行的《bE交响乐》的乐队配置的创作经历。其中谈到他在创作中处理民歌的经验:“归纳起来,民歌给我的影响是它的本质、色彩、特点至独特的风味,而我则以之纳入某一种曲式里头,以和声及作曲技巧去处理它。”马思聪在文末深情地写到:“我想,在交响乐里,我该写我们这浩大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光荣。”
马思聪夫妇第三次抵桂林,因媒介没有报道,笔推测是1943年2月下旬。因为1943年3月6日及7日,马思聪小提琴演奏会再一次在国民戏院举行之时,桂林版《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赖恩(英)神父的《贝多芬D长调协奏曲》的文章,介绍了这首著名小提琴协奏曲的曲调,曲式结构及作者生平,而当天的演奏会上,马思聪演奏的曲目中,恰恰就有这首乐曲。
除了演奏此曲之外,马思聪还演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柴可夫斯基闻名世界乐坛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波兰伟大的爱国作曲家肖邦的《祖国之歌》等。
1943年3月9日,马思聪夫妇再次应邀到桂林广播电台播奏了《狂热回旋曲》(门德尔松)、《圣母颂》(舒伯特)及《匈牙利圆舞曲》。同月14日,马思聪夫妇到桂林市中山中学,为师生们演奏了小提琴,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马思聪抗战期间在桂林文化城从事的音乐活动是多方面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尤其以小提琴音乐演奏会为最。他那颤动着的激情的琴弦在抗日烽烟里鼓舞着人民。据笔者粗略的统计,抗战以来,自1937年9月4日陆华柏、张源吉、沈承明、杨振锋、祁文桂五位音乐家组成的雅乐五人团假广西省政府礼堂举办的第一场专业音乐会算起,直到1944年9月8日(桂林紧急疏散当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为响应援助贫病作家(王鲁彦等)募散,在社会服务处举办的“姚牧歌乐会”止,桂林共举办过近120台、280场次的专业音乐会。其中马思聪是在文化城里举办个人音乐会最多,也是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从1941年6月20日至1943年6月7日止,短短的两年内,马思聪夫妇在桂林共举行了4台9场音乐会,并到桂林广播电台播奏了2次。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城,举办如此多的音乐会,在思马聪一生的艺术生涯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上个世纪50年代初,马思聪再一次到这座刚解放不久的城市举办音乐会。马思聪的琴声,马思聪的音乐,永远在桂林这座山清水秀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上空回荡……
上一篇:马思聪抗战时期在桂林的音乐活动
下一篇:致桂林二星导游莫素平的感谢信